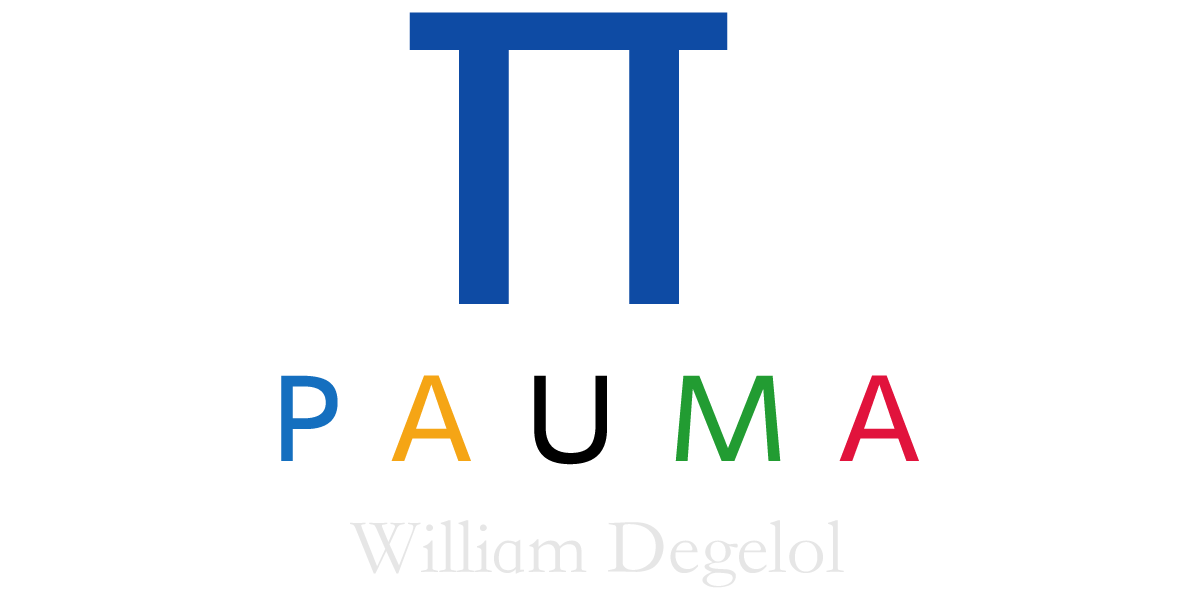René Descartes - Wikipedia
《1637谈谈方法》
第一部分
良知,是人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具有非常充分的良知,
就连那些在其他一切方面全都极难满足的人,也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的良知不够,要想再多得一点。
这一方面,大概不是人人都弄错了,倒正好证明,那种正确判断、辨别真假
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本来就是人人均
等的;我们的意见之所以分歧,并不是由于有些人的理性多些,有
些人的理性少些,而只是由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
对象不是一回事。因为单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
运用才智。杰出的人才固然能够做出最大的好事,也同样可以做
出最大的坏事;行动十分缓慢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
比离开正道飞奔的人走在前面很多。
关于哲学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看到它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能人
钻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所以我不敢
希望自己在哲学上的遭遇比别人好:我考虑到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许
多不同的看法,都有博学的人支持,而正确的看法却只能有一种,所以
我把仅仅貌似真实的看法一律看成大概是虚假的。
至于其他的学问,既然它们的本原是从哲学里借来的,我
可以肯定,在这样不牢固的基础上决不可能建筑起什么结实的东
西来。这类学问所能提供的名利,是不足以促使我去学习它们的,
因为谢天谢地,我并不感到境遇窘迫,要拿学问去牟利,以求改善
生活;我虽不像犬儒派那样自称藐视荣誉,对于那种只能依靠虚
假的招牌取得的名声我是很不在意的。最后说到那些骗人的学
说,我认为已经摸清了它们的老底,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不管它是
炼金术士的包票,还是占星术士的预言,是巫师的鬼把戏,还是那
些强不知以为知的家伙的装腔做势、空心牛皮。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
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吁以在自己心里或
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于是
趁年纪还轻的时候就去游历,访问各国的宫廷和军队,与气质不
同、身分不同的人交往,搜集各种经验,在碰到的各种局面里考验
自己,随时随地用心思考面前的事物,以便从中取得教益。因为在
我看来,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
多得多:普通人是对切身的事情进行推理,如果判断错了,它的结
果马上就会来惩罚他;读书人是关在书房里对思辨的道理进行推
理,思辨是不产生任何实效的,仅仅在他身上造成一种后果,就是
思辨离常识越远,他由此产生的虚荣心大概就越大,因为一定要花
费比较多的心思,想出比较多的门道,才能设法把那些道理弄得好
像是真理。我总是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会分清真假,以便在行动中
心明眼亮,一辈子满怀信心地前进。
第二部分
拿人的事情来说,我认为,斯巴达之所
以曾经十分强盛,并不是因为它的每一条法律都好,其中就有许多
条非常古怪,甚至违反善良的风俗(公妻,鼓励小偷);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它的
全部法律是由一个人制定的,是为着同一个目的的。我又想到,
书本上的学问,至少那些只说出点貌似真实的道理、却提不出任何
证据的学间,既然是多数人的分歧意见逐渐拼凑堆砌而成的,那就
不能像一个有良知的人对当前事物自然而然地作出的简单推理那
样接近真理。我还想到,既然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以前都当过儿童,
都不能不长期受欲望和教师的支配,教师们的意见又常常是互相
抵触的,而且谁的教导都未必总是正确,那么,我们的判断要想一
尘不染,十分可靠,就像一生下来就完全运用理性、只受理性指导
一样,那是简直不可能的。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谁把全城的房屋统统拆光,只是打算换过
样式重建,把街道弄漂亮;可是常常看到许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拆
掉,打算重盖,也有时候是因为房子要塌,或者房基不固,不得不
拆。以此为例,我相信:个人打算用彻底改变、推翻重建的办法改
造国家,确实是妄想;改造各门学间的主体,或者改造学校里讲授
各门学间的成规,也是同样办不到的;可是说到我自己一向相信的
那些意见,我却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把它们一扫而空,然后才能
换上好的,或者把原有的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我深信,用这种
办法做人,得到的成就一定可观,大大超过死守旧有的基础、一味
依赖年轻时并未查明是否真实就贸然昕信的那些原则。因为我虽
然看到这样做有种种困难,那些困难却不是无法克服的,并不像涉
及公众的事情那样,哪怕鸡毛蒜皮,改革起来都困难无比。那些大
体制推倒了就极难扶起,甚至动摇了就极难摆稳,而且垮下来是十
分可怕的。至于它们的毛病,那是有的,单凭它们的分歧就足以肯
定它们有毛病,可是习惯确实已经使毛病大大减轻,甚至在不知不
觉中使大量毛病得以免除,或者得到改正,我们凭思虑是做不到那
么好的。而且,沿用旧体制几乎总是比改换成新体制还要好受一
些;旧体制好比盘旋山间的老路,走来走去就渐渐平坦好走了,还
是照着它走好,不必翻大山过深沟抄直走。
因此,有些人飞扬浮躁,门第不高,家货不厚,混进了官场,却老
想改革政治,我是决不能赞成他们的。我要是想到这本书里有一点
点东西可以令人怀疑我有那么愚蠢,我就会十分懊悔让它出版了。
我的打算只不过是力求改造我自己的思想,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基
地上从事建筑。尽管我对自己的工作相当满意,在这里向大家提出
一个样品,这并不表明我有意劝别人学我。那些得天独厚的人也许
会有比我高明的打算,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很担心我这个打算
已经太大胆了。单拿下决心把自己过去听信的意见统统抛弃这一点说,
就不是人人都应当效法的榜样。世界上的人大致说来只分为两类,
都不宜学这个榜样。一类人自以为高明,其实并不那么高明,
既不能防止自己下仓促的判断,又没有足够的耐性对每一件事全都有条有理地思想,
因此,一旦可以自由地怀疑自己过去接受的原则,脱离大家所走的道路,
就永远不能找到他所要走的捷径,一辈子迷惑到底。另一类人则相当讲理,
也就是说相当谦虚,因而认定自己分辨真假的能力不如某些别人,
可以向那些人学习,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满足于听从那些人的意见,
不必自己去找更好的了。
至于古代人的分析和近代人的代数,都是只研究非常抽象、 看来毫无用处的题材的,
此外,前者始终局限于考察图形,因而只有把想像力累得疲于奔命才能运用理解力;
后者一味拿规则和数 字来摆布人,弄得我们只觉得纷乱晦涩、头昏脑胀,
得不到什么培养心灵的学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到要去寻找另外一种方法,
包含这三门学问的长处,而没有它们的短处。我知道,法令多如牛毛,每每执行不力;
一个国家立法不多而雷厉风行,倒是道不拾遗。所以我相信,
用不着制定大量规条构成一部逻辑,单是下列四条,只要我有坚定持久的信心,
无论何时何地决不违犯,也就够了。
1.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
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
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
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2.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
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3.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
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
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4.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
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我看到,几何学家通常总是运用一长串十分简易的推理完成
最艰难的证明。这些推理使我想像到,人所能认识到的东西也都
是像这样一个连着一个的,只要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且
一贯遵守由此推彼的必然次序,就决不会有什么东西遥远到根本
无法达到,隐蔽到根本发现不了。要从哪些东西开始,我觉得并不
很难决定,因为我已经知道,要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东西开始。
我考虑到古今一切寻求科学真理的学者当中只有数学家能够找到
一些证明,也就是一些确切明了的推理,于是毫不迟疑地决定就从
他们所研讨的这些东西开始,虽然我并不希望由此得到什么别的
好处,只希望我的心灵得到熏陶,养成热爱真理、厌恶虚妄的习惯。
但是我并不打算全面研究一切号称数学的特殊学问。我看出这些
学问虽然对象不同,却有一致之处,就是全都仅仅研究对象之间的各种关系或比例。
所以我还是只从一般的角度研究这些关系为好,不要把它们假定到某种对象上面,
除非那种对象能使我们更容易认识它们,更不要把它们限制到某种对象上面,
这样,才能把它 们同样恰当地应用于其他一切对象。我又注意到,为了认识这些关系,
我有时候需要对它们一一分别研究,有时候只要把它们记住,或者放在一起理解。
所以我想:为了便于分别研究它们,就该把它们假定为线的关系,
因为我发现这是最简单的,最能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想像和感官面前;
另一方面,为了把它们记住或者放在 一起研究,就该用一些尽可能短的数字来说明它们;
用这个办法,我就可以从几何学分析和代数里取来全部优点,
而把它们的全部缺点互相纠正了。
第三部分
我们知道,在重建住宅之前,光把旧房拆掉,备上新料,请好建
筑师,或者亲自设计,并且仔细绘出图纸,毕竟还是不够的,还应该
另外准备一所房子,好在施工期间舒舒服服地住着。所以,当我受
到理性的驱使、在判断上持犹疑态度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在行动上
犹疑不决,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地活着,我给自己定下了一套
临时行为规范,一共只有三四条准则,我愿意把它的内容告诉大家 。
第一条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
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明智的人为榜样,
遵奉他们在实践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
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白己。因为我虽然为了重新审查自己的全部意见,
从那时起把它们一律当成一文不值,却深信最好还是遵从最明智的人的看法。
尽管波斯和中国也许跟我们这里一样有很明智的人,我觉得还是
效法自己周围的人好处最大。而且,要想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
一定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不能光听他们说的话,这不仅是由于世风日下,
有不少人不肯全说真心话,也是由于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心是什么;
因为相信一件事并不等于知道自己相信这件事,这是两种思想活动,常常分道扬镰。
在那些有同样多的人接受的看法当中,我总是选择最合乎中道的。
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看法永远最便于实行,既然偏激通常总是坏的,
大概这也就是最好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可以在犯错误的时候不致离开正道过远:
万一我选择了一极端,应当走的却是另一极端,那就糟了。
而且我特别认为属于偏激的是各种限制我们某项自由的诺言。
这并不是我不赞成法律允许人们赌咒发誓、订立必须信守不渝的契约,
以防止不坚定的人反复无常,保证达到某种正当目的,如保证公平交易之类。
正好相反。这只是因为我看到,世界上的一切,特别是我这个人,并不是永远保持原状的。
拿我来说,就希望把自己的判断弄得越来越完善,并不希望把它弄糟,
如果由于曾经赞成过某件事,后来事情变了样我还只好说它对,
我认为那就是犯了违背良知的大错,我要变卦,不认为它对。
我的第二条准则是: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
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 这样做是效法森林里迷路的旅客,
他们决不能胡乱地东走走西撞撞, 也不能停在一个地方不动,
必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尽可能笔直地前进,尽管这个方向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偶然选定的,
也不要由于细小的理由改变方向,因为这样做即便不能恰好走到目的地,
至少最后可以走到一个地方,总比困在树林里面强。为人处世也是这样,我们的行
动常常必须当机立断,刻不容缓。有一条非常可靠的真理,
就是在无法分辨哪种看法最正确的时候必须遵从或然性最大的看法,
即便看不出哪种看法或然性大些也必须选定一种,然后在实践中不再把它看成可疑的,
而把它当作最正确、最可靠的看法,因为我们选定这种看法的理由本来就是如此。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从那时起就不犯后悔的毛病,不像意志薄弱的人那样反复无常,
一遇风吹草动就改变主意,今天当作好事去办的明天就认为很坏。
我的第三条准则是: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
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总之,要始终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
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作主。所以,我们对自身以外的事情尽了全力之后,
凡是没有办到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消除痴心妄想,凡是得不到的东西就不要盼望将来把它弄到手;
这样也就安分守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的意志所能要求的,
本来只是我的理智认为大致可以办到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身外之物一律看成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的东西,那么,
在平白无故地被削除封邑的时候,
就决不会因为丧失那份应当分封给我这位贵族的采地而懊恼,
就像不会因为没有当上中国皇帝或墨西哥国王而懊恼一样;
推而广之,生了病也就不会妄想健康,坐了牢也就不会妄想自由,
就像不会妄想生成金刚不坏之身、长出高飞远翥的翅膀一样。不过我也承认,
一定要经过长期训练,反复思考,才能熟练地从这个角度去看万事万物。
我相信,那些古代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摆脱命运的干扰,漠视痛苦和贫困,
安乐赛过神仙,其秘密主要就在于此。 因为他们不断地考察自然给他们划定的界限,
终于大彻大悟,确信 除了自己的思想之外,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由他们作主,
确信只要认清这一点就可以心无挂碍,不为外物所动;
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作出了绝对的支配,因此也就有理由认为自己又富又强,逍遥安乐,
胜过所有的别人,别人不懂这种哲学,不管得到自然和命运多大优待,
还是不能支配一切、事事如愿以偿的。
以后整整九年,我只是在世界上转来转去,遇到热闹戏就看一看,只当观众,不当演员。
对每一个问题我都仔细思考一番,特别注意其中可以引起怀疑、可以使我们弄错的地方,
这样,就把我过去马马虎虎接受的错误一个一个连根拔掉了。我这并不是模仿怀疑论者,
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摆出永远犹疑不决的架势。 因为事实正好相反,
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
这样做我觉得相当成功,因为我对命题进行审查、揭露其错误或不确之处的时候,
用的并不是软弱无力的猜测,而是明白确切的推理;我发现任何一个命题,
不管如何可疑,总可以从其中推出一点相当可靠的结论来,
哪怕那个命题本身是一点都不可靠的。
人们拆除旧房的时候,总是把拆下的旧料保存起来,利用它盖新房。我也是这样办的。
我断定自己的某种看法根据不足,把它取消不要的时候,总是从各方面
观察,取得若干经验,这些经验后来都有助于建立更可靠的看法。
此外我还继续练习我所制定的那种方法,因为我不仅从一般的方面着手,
按照那些规则仔细地运用我的全部思想,而且还随时留下 一点时间,
从特殊的方面着手,解决了某些数学上的难题,甚至解决了某些其他科学上的难题;
我发现那些问题所依据的本原不够牢靠,使它们脱离了那些本原,
就把它们弄得几乎跟数学问题差不多了。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见到许多实例,
说明我是怎样做的。 如此看来,我的生活方式表面上跟某些人没有什么两样:
不做什么事情,只是愉快地、正派地过着日子,用心把欢乐和邪恶分开;
为了不至于闲得无聊,从事着各种正当的娱乐。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在执行我的计划,
增进我对真理的认识,成绩也许比埋头读书、只跟读书人往来还要大些。
第四部分
可是现在我的目的是专门寻求真理,我想做法就完全相反:任何一
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像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该把它当成绝对
虚假的抛掉,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心里是不是还剩下→点东西完
全无可怀疑。因此,既然感官有时欺骗我们,我就宁愿认定任何东
西都不是感官让我们想像的那个样子。既然有些人推理的时候出
错,连最简单的几何学问题都要弄乱,作出似是而非的推论,而我
自己也跟别人一样难免弄错,那我就把自己曾经用于证明的那些
理由统统抛弃,认为都是假的。最后我还考虑到,我们醒时心里的
各种思想在睡着时也照样可以跑到心里来,而那时却没有一样是
真的。既然如此,我也就下决心认定:那些曾经跑到我们心里来的
东西也统统跟梦里的幻影一样不是真的。可是我马上就注意到:
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
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
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
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
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
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个命题之所以使我确信自己说的是真理,
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是,才能想。因此我认为可以一般地规定:
凡是我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
不过,要确切指出哪些东西是我们清楚地理解的,我认为多少有点困难。
我拿几何学家们的对象来研究,把它看成一个连续体,
一个在长、宽、高三方面无限伸张的空间,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
这些部分可以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而且可以用各种方式挪动戎移置,
因为几何学家就是这样设定的。我浏览了几个最简单的证明,
注意到它们之所以被人们公认为十分可靠,只是由于按照我们刚刚说过的那条规则,
大家都明确地理解了它们。我也注意到,这些证明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使我确信
它们的对象是存在着的。因为我很清楚地看出,只要设定→个三
角形,它的三只角就必定等于两直角,可是我并没有因此看出什么
东西使我确信世界上有二三角形。然而,我回头再看我心里的一个完满的是者的观念时,
却发现这个观念里已经包含了存在,就像三角形的观念包含着它的二只角等于两直角、
球形的观念包含着球面任何一点都与球心等距离一样,甚至于还要更明确。
由此可见,神这个极完满的是者是或者存在,这个命题至少同几何学上任何
一项证明同样可靠。
可是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很难认识这条真理,甚至很难认识自己的灵魂是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鼠目寸光,只看到可以感觉到的 东西,养成一种习惯,
完全用想像力考虑问题,而想像是一种用于物质性的东西的特殊思想方式,
所以凡是不能想像的事情他们就觉得无法理解。这种倾向,
在经院哲学家信奉的一条格言里表现得相当明显,
他们说:理智中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曾在感官中。
实际上,神的观念和灵魂观念在感官中是根本没有的。我觉得,
那些人要想用想像来理解这两个观念,实在无异于要用眼睛来听声音、 闻气味;
只是还有这样一点区别:视觉同嗅觉或听觉一样使我们相信它的对象是真的,
然而我们的想像、我们的感官如果没有理智参与其事,并不能使我们相信任何东西。
最后可能还有些人听了我说的这番话之后对神和灵魂的存在仍然不很信服。
我很愿意告诉他们:有许多别的事情他们也许认为十分确实,例如我有一个身体、
天上有一些星星、有一个地球之类,其实全都不甚可靠;
因为尽管我们对这类事情有一种实际行动 上的确信,谁要是敢于怀疑它们至少显得很狂妄,
可是问题一涉及 形而上学上的确实可靠,情形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如果注意到,
我们睡着的时候也照样可以想像到这类事情,例如梦见自己有另外一个身体、
天上有另外一批星星、有另外一个地球之类,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么,
只要他不是神经错乱,就一定会承认我们有充分理由对那类事情不完全相信了。
因为梦中的思想常常是生动鲜 明的,并不亚于醒时的思想,我们又怎么知道前者是假的、
后者不是假的呢?这个问题,高明的人可以尽量钻研,爱怎么研究就怎么
研究。我相信,如果不设定神的存在作为前提,是没有办法说出充分理由来消除这个疑团的。
因为首先,就连我刚才当作规则提出的那个命题:
“凡是我们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
其所以确实可靠,也只是由于神是或存在,神是一个完满的是者,
我们心里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由此可见,我们的观念或看法,光从清楚分明这一点看,
就是实在的、从神那里来的东西,因此就只能是真的。
这样看来,如果说我们常常有一些观念包含着虚妄,那就只能是那些混乱模糊的观念,
因为它们从不是者(者的反面)分沾了这种成分;也就是说,那些观念在我们心里那样模糊,
只是由于我们并不是十分完满的。因为很明显,说虚妄、不完满本身来自神,
其不通并不亚于说真理、完满来自不是者。
可是,如果不知道自己心里真实的东西是来自一个完满的、无限的是者的,
尽管我们的观念清楚分明,我们还是没有理由确信这些观念具有真实这一完满品质的。
我们认识了神和灵魂、从而确定了那条规则之后,就很容易明白,
我们睡着时想像出来的那些梦想,决不能使我们怀疑自己醒时的思想不真。
因为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可以出现非常清楚的观念,
例如几何学家就可以在梦中发现新的证明,
人尽管在做梦,观 念并不因此就不是真的;
我们梦中最常犯的错误是用外部感官的那种方式表现各式各样的对象,这也不坏,
可以引起我们对感性观念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因为这类观念在我们醒时也常常欺骗我们,
例如黄疸病人就觉得什么都是黄的,距离很远的星星或其他形体
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比实际上小得多。
总之,不管醒时睡时,我们都只能听信自己理性提供的明证。
请注意我说的是理性,并不是想像,也不是感官。例如,我们虽然十分清楚地看见太阳,
却不能因此断定太阳就像我们看见的那么大;
我们可以非常分明地想像到狮子脑袋接在羊身子上,
却不能就此推出世界上真有一个四不像。因为理性并没有向我们发出指示,
说我们这样看到或想像到的就是真相。可是它却明白地指示我们:
我们的一切观念或看法都应当有点真实的基础,因为神是十分完满、十分真实的,
决不可能把毫无真实性的观念放到我们心里来。然而在睡着的时候,
我们的想像虽然有时跟醒时一样生动鲜明,
甚至更加鲜明,我们的推理却决没有醒时那么明确,
那么完备,所以理性又指示我们:我们的思想不可能全都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十分完满的;真实的思想一定要到醒时的思想里去找,不能到梦里去找。
第五部分
《论世界,或论光》那部书的论述对象是各种物质性
的东西的本性。我在动手写它之前,曾经打算把这一方面我认为知
道的东西统统写进去。然而,画家是不能在一个平面上把立体的各
方面同等地表现出来的,只有从其中选择一个主要方面正对着光
线,把其他的方面都放在背阴处,使人们看正面的时候可以附带看
到侧面。同样情形,我的论述里也无法包罗我的全部思想,所以我
只用较大的篇幅表达我对光的理解,然后附带讲一讲太阳和恒星,
因为光几乎全部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再讲一讲天字,因为它是传导
光的;再讲一讲行星、彗星和地球,因为它们是反射光的;再专门讲
一讲地球上的各种物体,因为它们有的是有色的,有的是透明的,有
的是发光的;最后讲一讲人,因为他是这些东西的观察者。
如果我们研究心脏的温度是怎样传到其他肢体上去的,
那就必须承认这是凭借血液,血液经过心脏变热,再从那里带着温度流到全身;
因此,如果把身体上某个部分的血弄掉,那个部分也就变凉了;
心脏尽管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如果不把新的血液不断输送到手脚上去,
还是不足以使手脚变热的。我们又由此认识到,
呼吸的真正用途就在于往肺里运送足够的新鲜空气,血液在心脏里已经稀化成为蒸汽,
从右腔进入两肺,遇到空气就浓缩起来,重新变成血液,然后回到左腔,
这样才能给那里的火当燃料。
如果有那么一些机器,其部件的外形跟猴子或某种无理性动物一模一样,
我们是根本无法 知道它们的本性与这些动物有什么不同的;
可是如果有一些机器 跟我们的身体一模一样,并且尽可能不走样地模仿着我们的动作,
我们还是有两条非常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明它们并不因此就是真正的人。
第一条是:它们决不能像我们这样使用语言,或者使用其他由语言构成的讯号,
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台机器,构造得能够吐出几个字来,
甚至能够吐出某些字来回答我们扳动它的某些部件的身体动作,
例如在某处一按它就说出我们要它说的要求,在另一处一按它就喊痛之类,
可是它决不能把这些字排成别的样式适当地回答人家向它说的意思,
而这是最愚蠢的人都能办到的。第二条是:那些机器虽然可以做许多事情,
做得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好,甚至更好,却决不能做别的事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它们的活动所依靠的并不是认识,而只是它们的部件结构;因为理性是万能的工具,
可以用于一切场合,那些部件则不然,一种特殊结构只能做一种特殊动作。
由此可见,一台机器实际上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部件使它在生活上的各种场合全都应付裕如,
跟我们依靠理性行事一样。而且,依靠这两条标准我们还可以认识人跟禽兽的区别。
因为我们不能不密切注意到; 人不管多么鲁钝、多么愚笨,连白痴也不例外,
总能把不同的字眼排在一起编成一些话,用来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
可是其他的动物相反,不管多么完满,多么得天独厚,全都不能这样做。
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缺少器官,因为我们知道,八哥和鹦鹉都能像我们这样吐字,
却不能像我们这样说话,也就是说,不能证明它们说的是心里的意思;
可是先天聋哑的人则不然,他们缺少跟别人说话的器官,在这一点上跟禽兽一样,
甚至不如禽兽,却总是自己创造出一些手势把心里的意思传达给那些
跟他们常在一起并且有空学习他 们这种语言的人。这就证明禽兽并非只是理性不如人,
而是根本没有理性,因为学会说话是用不着多少理性的;
我们虽然看到那些同种的动物也跟人一样彼此能力不齐,有比较容易训练的,
有比较笨的,可是最完满的猴子或鹦鹉在学话方面却比不上最笨的小孩,
连精神失常的小孩都比不上;如果不是动物的灵魂在本性上跟我们完全不同,
这是无法想像的。我们决不能把语言与表现感情的自然动作混为一谈,
那些动作动物是可以模仿的,机器也同样可以模仿;我们也不能像某些古人那样,
认为禽兽也有语言,只是我们听不懂。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禽兽既然有许多器官跟我们相似,
它们就能够向我们表达思想,如同向它们的同类表达一样了。还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注意,
这就是:虽然有许多动物在它们的某些活动上表现得比我们灵巧,可是我们看到,
尽管如此,这些动物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却并不灵巧:它们做得比我们好并不证明它们有心思;
因为它们假如有就会比我们任何人都强,就会在一切其他事情上做得都好;
可是它们并没有心思,是它们身上器官装配的本性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看到一架时钟由齿轮和发条组成,就能指示钟点、 衡量时间,
做得比我们这些非常审慎的人还要准确。
第六部分
我深信:任何一个人,包括医务人员在内,都不会不承认,医学上已经知道的东西,
与尚待研究的 东西相比,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如果我们充分认识了各种疾病的原因,
充分认识了自然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药物,我们是可以免除无数种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甚至可以免除衰老,延年益寿的。
我自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毕生精力用来寻求一门非常必要的学问,
并且已经摸到了一条途径,觉得非常可靠,只要照着走,必定可以万无一失地把它找到;
只是受到两方面的阻碍,一是生命短促,二是经验不足。所以我认为,要排除这两重障碍,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 己所发现的一点东西毫无保留地、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
请求有志之士继续努力,更进一步,按照各人的倾向和努力从事必要的实验,
把自己获得的经验再告诉大家,代代相传,使后人能够接过前人的火炬前进,
把多数人的生命和成绩汇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群策群力,就可以大有作为,
远非个人单干所能比。
关于经验,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认识越进步越需要经验。 我们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宁可采用那些举目可见、尽人皆知的经验;但要略加思考,不必好高鸯远,
追求罕见的冷僻经验。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最通常的原因,
遇见罕见的经验每每会上当,而且那种经验所依靠的条件几乎总是很特殊、很琐屑的,
很不容易看出来。我在这方面采取了以下的步骤:首先,我一般地考察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以及能够有的一切,设法找出它们的本原或根本原因,为了这个目的,我不考虑别的,
只考虑它们是神一手创造出来 的,不从别处寻找,只发掘我们灵魂深处固有的真理萌芽,
从其中抽绎出这些原因。跟着我就细看,根据这些原因可以推出哪些第一步的、
最通常的结果;我觉得这样做已经发现了天宇、星辰、地球,甚至于发现了地球上的水、
空气、火、矿物之类,这都是最普通、 最简单的东西,因此也最容易认识。
然后我就想再往下推,推出更 特殊的东西,这时候我面前出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事物,
使我感到 在地球上现存的物种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物种,
如果神的意志要把它们放在地球上供我们使用的话,也可能在地球上存在过,
单凭人的思想实在分不清哪是现存的,哪是可能存在过的,所以只有通过结果往上追溯原因,
只有进行许多特殊的实验。这以后,我又用我的心灵进行复查,我敢大胆地说,
凡是曾经在我的感官面前出现的事物,
我发现没有一样不能用我找出的那些本原相当方便地加以说明。
可是我也必须承认,自然界的势力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广的,那些本原是非常简单、
非常一般的。因此我发现,几乎任何一个特殊结果,
开头我都觉得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从那些原因推出来,
我通常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能决定它究竟依靠其中的哪一种方式;
为了解除这个困难,我认为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安排一套实验,
根据实验结果不同来决定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解释。 到了这一步,我觉得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应当从什么角度进 行大部分实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可是我也同样看到,
这些实验非常繁重,数量非常庞大,我只有两只手,只有那么一点收入,
纵然再多十倍,也无法把它们做完;因此,我在认识自然方面能有多大进展,
就看我今后能有条件做多少实验。我写那部论著就是打算使大家了解这一点,
并且明白指出这样做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大好处,所以我要求一切有志为人群谋福利的人,
也就是那些并非沽名钓誉、亦非徒托虚名的真君子,
把他们已经做出的实验告诉我,并且帮助我研究如何进行新的实验。
藤萝是决不能爬得比自己依附的树更高的,而且常常在爬到树顶之后又往下爬,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是在走下坡路,就是说,他们如果不再钻研,学问也就江河日下,
不如另外一批人,读完经典里明白说出的东西还不满足,又想出许多难题,
要在字里行间搜索,找出祖师爷没有说的、甚至根本没有想到的解答。
他们那种研究哲学的方式是非常适合才智十分平庸的人的,
因为他们使用的范畴和原理含含糊糊,
使他们能够放言高论, 无所不谈,就像真的知道似的,并且能够为他们的全部说法辩护,
对抗各种最巧妙、最灵活的说法,弄得人家无可奈何。他们这样做,我觉得好像一个瞎子,
为了跟看得见的人打架不吃亏,就把人家拉到很黑很黑的地窖底下去。
可以说,我不肯发表我所用的那些哲学原理,对这种人是很有利的,
因为那些原理非常简单,非常明确,我一发表就等于打开窗子,
把阳光放进他们跑下去打架的那个地窖。就连那些最聪明的人也大可不必急于知道那些原理,
因为如果他们要想知道怎样放言高论,无所不谈,赢得博学的名声,
那很容易达到目的,只要守住貌似真实的道理就行了,这是在哪种对象里都找得到的,
不用多费气力,不像寻求真理那样难。真理是只能在某些对象里一点一点发现的,
如果要谈的是别的对象,那就要求我们坦白承认自己不知道。
如果他们并不想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唬人,
真想知道那么一点真理(那点真理当然是值得知道的),
真想照着我那样的计划去做,那很好办,看看这篇谈话里说过的那些就行了,
并不需要我再多说些什么。因为,如果他们能力很强,可以取得的成就比我大,
那就更不用说,我认为已经发现的东西他们自己也一定可以发现。
既然我的研究工作一贯循序渐进,尚待发现的东西自然比已经找到的东西更困难、
更深奥,他们自己去发现它一定比跟我学更痛快;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养成一种习惯,
先从简单的东西开始,然后一步一步进而探索比较困难的问题,
这比我的全部教导对他们更有用。拿我自己来说,我相信,
如果在幼年的时候人家就把我多年来没法加以证明的那些真理全部教给了我,
学得一点都不费力,大概我是决不会知道什么别的真理的,
最低限度在寻求新的真理的时候决不会总是那样熟练、那样得心应手的。
总之,如果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工作,由原班人马一直干到底不另换人可以完成得更好,
那就是我所干的这一种。
可是,为了完成这种工作,需要进行一些实验,那些实验凭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无法做完;
一个人能够有效地使唤的只是自己的一双手,此外就只有找一些匠人或愿意受雇的人,
利用他们希望得 钱的心理,拿出这种最有效的办法,让他们严格按照规定完成任务。
也可能有一些人出于好奇,或者想学点东西,自愿给他出力帮忙,
可是这类人通常总是说的多、做的少,只是提出一些根本办不到的建议,
其目的当然是以此为由,要他给自己讲解几个难题,至少也要恭维自己几句,
应酬一番,作为报答,干这类事情就不能不耗费若干有用的时间。
至于别人已经做出的实验,把它看成秘密的人是决不会公开的,
即便有人愿意告诉他一些,也多半内容驳杂,含有大量无用的枝节、多余的成分,
很不容易辨认出真理来;而 且他还会发现,由于实验者竭力把结果描述得符合自己的原则,
这些实验几乎全都被解释糟了,甚至弄得错误百出,即或有些实验对他有用,
也必须花费时间挑选,实际上得不偿失。因此,假如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
大家确实知道他能够作出最伟大的发现,给公众带来莫大的利益,由于这个缘故,
别人都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完成计划,依我看来,能帮得上他的也只限于提供经费,
资助他进行必要的实验,再就是谁也不要打扰他、浪费他的时间。
何况我这个人还没有那么大的魄力,不敢保证自己的贡献一定出乎寻常,
也没有那么大的派头,不敢想像大家都应当很关心我的计划,我的人格也不是十分卑鄙,
那些可以被人认为非分的照顾我是一样都不肯接受的。
要知道,别人花二十年工夫想出来的东西只要告诉他们两三个字,
他们就立刻以为自己在一天之内全都知道了;这种人越聪明、越机灵,就越容易犯错误,
越不能发现真理,我要是作了那种推演,他们就会抓住把柄,认为那就是我的原理,
在上面胡乱建立起狂妄的哲学来,弄得人家以为是我犯了错误。
至于那些纯粹属于我的看法,我承认它们是新的,并不辩解,
因为我相信大家看清了我的推理就会发现这些看法非常简单、非常合乎常识,
同大家对这类问题所能采取的其他见解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奇怪;
我也不吹嘘这是我的创见,不过我很自豪,我采取这些看法并不是由于别人这样说过,
也不是由于别人没有这样说过, 而只是由于理性这样说服了我。
如果匠人不能立刻把《折光学》里讲解的那种发明用于实际,
我想决不能就此便说那种发明很糟,因为一定要有熟练的技巧,
才能把我所描述的那些机械制造出来、装配起来、做到毫无缺陷。
如果一做就成,我觉得倒是一件怪事,不亚于一个人光凭一本好乐谱学了一天
就会弹出一手好琵琶。我用本国的语言法文写这本书, 没有用师长的语言拉丁文写,
那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单凭自己干干净净的天然理性来判断的人一定善于评判我的看法,
胜过只信古书的人;至于那些把良知与学习结合起来的人,是我一心向往的公正评判者,
我相信他们决不会如此偏爱拉丁文,由于我用俗语说理就掩耳不听。
附录一
我曾经想到首先要在那里说明哲学是什么,从一些最平常的
事情说起,例如=哲学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研究智慧,所谓智慧指的并不只是处事审慎,
而是精通人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处理生活、 保持健康和发明各种技艺;
这种知识要能够做到这样,必须是从一些根本原因推出来的。
所以,要研究怎样取得这种知识,一个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根本原因,
也就是本原;而这些本原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非常清楚,非常明显,
人心一注意到它们就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性;另一个是要依靠它们才认识其他事物,
就是说,离开其他事物能够认识它们,而不是反过来离开它们能够认识其他事物;
这以后就该尽量努力,从这些本原推演出各种依靠它们的事物的知识,
做到推演系列中没有一个环节不十分明显。确确实实,神是唯一完全智慧的,
就是说,他对一切事物的真理性具有全部知识;可是我们可以说,人是有或多或少的智慧的,
一视他们对那些最重要的真理具有或多或少的知识而定。
我相信这些话没有一点不是饱学之士们仍然不同意的。
我接着就请大家考虑这个哲学的用处,指出它既然遍及人心所能知道的一切,
我们就该相信,只是它使我们有别于那些生番和蛮子,每一个民族的文明与开化,
就是靠那里的人哲学研究得好, 因此一个国家最大的好事就是拥有真正的哲学家。
此外,对于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说,不仅跟进行这种研究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有益的,
自己亲身从事研究更是好到不知多少倍;毫无疑问,用自己的眼睛指导自己的行动,
以及用这种办法去享受颜色的美,享受光明,要比闭着两眼听别人指点好得多;
不过听从别人指引比起闭上两眼只听任自己行动还要好些。真正说来,活着不研究哲学,
就如 同闭上两眼不肯睁开;观看我们视觉发现的一切而得到的那种愉快,
根本比不上人们凭哲学发现事物的知识而获得的那种满足;
总之,我们必须研究哲学来砥砺德行、指导人生,胜过使用眼睛来引导我们走路。
野生的禽兽只有身体需要保护,就经常不断地从事寻求养身的食品;
然而人的主要部分是心灵,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求智慧上,智慧才是他真正的养料;
而且我也敢断言,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是不会失败的,只要他们抱着取得胜利的希望、
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多少就行。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如此卑下,牢牢地固守在各种感官对象上面,
不会有那么一回抛开感官对象,转过来希望取得另外一个更伟大的好东西,
尽管他每每不知道这个好东西在哪里。那些得天独厚的人享有充分的健康、荣誉和财富,
更不会缺少别人所有的那种欲望;正好相反,
我相信这些人是以极大的热忱期待着另外一个比他们具有的一切更伟大的好东西。
这个伟大的好东西,在那种不带信仰光辉的自然理性看来,
无非就是那种通过根本原因得到的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哲学所研究的那个智慧。
因为这些道理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它们不难使人信服,只要把它们很好地推演出来就行。
可是,由于人们凭经验不能相信这些说法,因为他们见到那些自命为哲学家的人常常
不如从未从事这种研究的人那么智慧、那么明理,
所以我就在这里扼要地说明了我们现有的全部学问状况如何,以及人们达到的智慧有哪几等。
第一等的只包含一些本身 就很清楚的见解,不用深思就能得到它们。
第二等的包括各种感官经验使我们知道的一切。第三等的是别人的谈话教给我们的。
此外还可以加上一个第四等的,就是读书,并不是读所有的书,
而是专指读那些能给我们教益的人写的书,因为这就是我们与作者进行的一种谈话。
在我看来,人们通常拥有的智慧只是用这四种办法取得的;
我在这里就不列入那种神圣的天启,因为天启并不是一步一步引导我们,
而是突然一下把我们提高到确信不移的状态的。在以往的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伟大的人物,
曾经努力寻求第五等办法来取得智慧,比其他四等要高明、精确到不知多少倍,
这就是寻找那些根本原因和真正的本原,从其中推演出人能知道的一切的所以然;
从事这种工作的,就是大家称之为哲学家的那些人。
( 苏格拉底的门徒)他们的门徒争执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对一切都怀疑,
还是认为某一些是确实可靠的。这就使争论的双方都陷入荒唐的错误:
因为有些主张怀疑一切的人一直怀疑到人的行为,因而放荡不羁,无意于谨言慎行;
那些主张确有其事的则以为确实与否应当取决于感官,因而对感官完全信任,
据说伊壁鸠鲁就敢于反对天文学家举出的全部理由,断言太阳并不比我们看到的大些。
我们发现, 在大多数争论中间,并不是真理位于人们主张的两种意见的中间所在,
不偏不倚,而是哪种意见越说得偏激就离真理越远。那些过于倒向怀疑方面的人的错误,
并不是长期得到人们信从,另一批人的错误,由于承认感官在许多事情上欺骗我们,
也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纠正。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把这种错误完全消除了,
我是向大家说明,确信并不是由感官得来的,只是由具有明显知觉的理智取得的;
我们只有来自上述四等智慧的知识时,不应该怀疑那些 有关人类行为的似乎真实的事情,
也不应该把它们看成十分确定,不能改变看法,哪怕在有某种理性的证据要我们改变的时候。
由于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虽然明白却不肯实行,
若干世纪以来大多数想当哲学家的人盲目追随亚里士多德,以至于常常歪曲他的著作的意思,
给他加上种种若他回到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承认属于他自己的意见;
那些没有跟随亚里士多德的人(其中有很多是颇有才智的)在幼时也不免感染上他的意见
(因为这是学校里教的唯一教材),
这就成了牢固的先入之见,使他们不能认识到真正的本原。
我虽然对他们很尊重,不愿因斥责他们而给自己招来怨恨,却能为我的说法提出一个证明,
就是我相信他们没有一个会不同意这个说法,即:
他们全都把一个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东西设定为本原。
例如,我知道他们全都设定了地上各种形体中的重量,
可是尽管经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号称沉重的形体向地心降落,
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所谓重量的本性是什么,也就是说,
不知道那使它们如此下落的原因或本原的本性是什么,这一点我们应该从别的地方去学。
这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说虚空和原子,热和冷,干和湿,盐、硫、 汞,
以及有人设定为本原的这一类东西。从一个不明显的本原推演出的一切结论也不能是明显的,
虽说是明显地推演出来的;由此可见,
根据这样的本原作出的一切推理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某物的可靠知识,
因此也不能使他们在智慧的研究中前进一步。尽管如此,
我并不想贬低他们每一位所能指望获得的荣誉,我只是想安慰一下那些不曾进行研究的人,
不得不说,这好像在旅行,如果背朝着要去的地方前进,走的时间越长、速度越快,
就离开目标越远,纵然后来走 上了正道,也不能立刻达到目的地,像以前没有走似的;
所以,如果 设定着那些坏的本原,越是反复琢磨它们,越是仔细从其中推出各种结论,
就离开认识真理和智慧越远。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
对那种迄今被称为哲学的东西学得越少,就越能学到真东西。
《1647反驳和答辩》
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
可是,虽然感官有时在不明显和离得很远的东西上骗过我们,
但是也许有很多别的东西,虽然我们通过感官认识它们,却没有理
由怀疑它们:比如我在这里,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
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
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除非也许是我和那些疯子相比?那
些疯子的大脑让胆汁的黑气扰乱和遮蔽得那么厉害,以致他们尽
管很穷却经常以为自己是国王;尽管是一丝不挂,却经常以为自己
穿红戴金;或者他们幻想自己是盆子、罐子,或者他们的身子是玻
璃的。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如果我也和他们相比,那么我
的荒诞程度也将不会小于他们了。
虽然如此,我在这里必须考虑到我是人,因而我有睡觉和在梦
里出现跟疯子们醒着的时候所做的一模一样、有时甚至更加荒唐
的事情的习惯。有多少次我夜里梦见我在这个地方,穿着衣服,在
炉火旁边,虽然我是一丝不挂地躺在我的被窝里!我现在确实以
为我并不是用睡着的眼睛看这张纸,我摇晃着的这个脑袋也并没
有发昏,我故意地、自觉地伸出这只手,我感觉到了这只手,而出现
在梦里的情况好像并不这么清楚,也不这么明白。但是,仔细想
想,我就想起来我时常在睡梦中受过这样的一些假象的欺骗。想
到这里,我就明显地看到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
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
来,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我现在是在睡
觉的程度。
那么让我们现在就假定我们是睡着了,假定所有这些个别情
况,比如我们睁开眼睛,我们摇晃脑袋,我们伸手,等等,都不过是
一些虚幻的假象;让我们就设想我们的手以及整个身体也许都不
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尽管如此,至少必须承认出现在我们的梦
里的那些东西就像图书一样,它们只有摹仿某种真实的东西才能
做成,因此,至少那些一般的东西,比如眼睛、脑袋、手,以及身体的
其余部分①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因
为,老实说,当画家们用最大的技巧,奇形怪状地画出人鱼和人羊
的时候,他们也究竟不能给它们加上完全新奇的形状和性质,他们
不过是把不同动物的肢体掺杂拼凑起来;或者就算他们的想象力
达到了相当荒诞的程度,足以捏造出来什么新奇的东西,新奇到使
我们连类似的东西都没有看见过,从而他们的作品给我们表现出
一种纯粹出于虚构和绝对不真实的东西来,不过至少构成这种东
西的颜色总应该是真实的吧。
因为,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
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
的一些真理,看来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
因为这些旧的、平常的见解经常回到我的思维中来,它们跟我
相处的长时期的亲熟习惯给了它们权利,让它们不由我的意愿而
占据了我的心,差不多成了支配我的信念的主人。只要我把它们
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那样来加以考虑,即像我刚才指出的那样,它
们在某种方式上是可疑的,然而却是十分可能的,因而人们有更多
的理由去相信它们而不去否认它们,那么我就永远不能把承认和
信任它们的习惯破除。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想,如果我反过来千
方百计地来骗我自己,假装所有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幻想出来
的,直到在把我的这些成见反复加以衡量之后,使它们不致让我的
主意偏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使我的判断今后不致为坏习惯所左右,
不致舍弃可以导向认识真理的正路反而误入歧途,那我就做得更
加慎重了。因为我确实相信在这条路上既不能有危险,也不能
有错误,确实相信我今天不能容许我有太多的不信任,因为现在的
问题还不在于行动,而仅仅在于沉思和认识。
因此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他是至
上的真理源泉),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
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天、空气、地、颜色、形
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
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③。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
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却错误地相信我有
这些东西。我要坚决地保持这种想法;如果用这个办法我还认识
不了什么真理,那么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断。就是因为这个原
故,我要小心从事,不去相信任何错误的东西,并且使我在精神上
做好准备去对付这个大骗子的一切狡诈手段,让他永远没有可能
强加给我任何东西,不管他多么强大,多么狡诈。
可是这个打算是非常艰苦吃力的,而且由于某一种惰性使我
不知不觉地又回到我日常的生活方式中来。就像一个奴隶在睡梦
中享受一种虚构的自由,当他开始怀疑他的自由不过是一场黄粱
美梦而害怕醒来时,他就和这些愉快的幻象串通起来,以便得以长
时间地受骗一样,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重新掉进我的旧见解中去,
我害怕从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害怕在这个休息的恬
静之后随之而来的辛勤工作不但不会在认识真理上给我带来什么
光明,反而连刚刚在这些难题上搅动起来的一切乌云都无法使之
晴朗起来。
论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认识
因此我假定凡是我看见的东西都是假的;我说服我自己把凡
是我装满了假话的记忆提供给我的东西都当作连一个也没有存在
过。我认为我什么感官都没有,物体、形状、广延、运动和地点都不
过是在我心里虚构出来的东西。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认为是真实
的呢?除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而外,也许再也没
有别的了。
可是我怎么知道除了我刚才断定为不可靠的那些东西而外,
还有我们不能丝毫怀疑的什么别的东西呢?难道就没有上帝,或
者什么别的力量,把这些想法给我放在心里吗?这倒并不一定是
这样;因为也许我自己就能够产生这些想法。那么至少我,难道我
不是什么东西吗?可是我已经否认了我有感官和身体。尽管如
此,我犹豫了,因为从这方面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难道我就是那
么非依靠身体和感官不可,没有它们就不行吗?可是我曾说服我
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
体;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对不;如果我
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我想到过什么东西,那么
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
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
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
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
所以,在对上面这些很好地加以思考,同时对一切事物仔细地加以
检查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成确定无疑
的,即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
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
可是我还不大清楚,这个确实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所
以今后我必须小心从事,不要冒冒失失地把别的什么东西当成我,
同时也不要在我认为比我以前所有的一切认识都更可靠、更明显
的这个认识上弄错了。
首先两个是吃饭和走路;可是,假如我真是没有身体,
我也就真是既不能走路,也不能吃饭。另外一个是感觉;可是没有身体就不能感觉,
除非是我以为以前我在梦中感觉到了很多东西,
可是醒来之后我认出实际上并没有感觉。
另外是思维。现在我觉得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只有它不能跟
我分开。有我,我存在这是靠得住的;可是,多长时间?我思维多
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思维,也许很可能我
就同时停止了存在。我现在对不是必然真实的东西一概不承
认;因此,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
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那么我是一个真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了;可是,是一个什么东
西呢?我说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还是什么呢?我要再发动
我的想象力来看看我是不是再多一点的什么东西,我不是由肢体
拼凑起来的人们称之为人体的那种东西;我不是一种稀薄、无孔不
入、渗透到所有这些肢体里的空气;我不是风,我不是呼气,不是水
汽,也不是我所能虚构和想象出来的任何东西,因为我假定过这些
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即使不改变这个假定,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确
实知道我是一个东西。
可是,能不能也是这样:由于我不认识而假定不存在的那些东
西,同我所认识的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一点也不知道。关于这
一点我现在不去讨论,我只能给我认识的那些东西下判断:我已经
认识到我存在,现在我追问已经认识到我存在的这个我究竟是什
么。可是关于我自己的这个概念和认识,严格来说既不取决于我
还不知道其存在的那些东西,也更不取决于任何一个用想象虚构
出来的和捏造出来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靠得住的。何况虚构
和想象这两个词就说明我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把我想象成一个
什么东西,那么实际上我就是虚构了,因为想象不是别的,而是去
想一个物体性东西的形状或影像。我既然已经确实知道了我存
在,同时也确实知道了所有那些影像,以及一般说来,凡是人们归
之于物体性质的东西都很可能不过是梦或幻想。其次,我清楚地
看到,如果我说我要发动我的想象力以便更清楚地认识我是谁①,
这和我说我现在是醒着,我看到某种实在和真实的东西,但是由于
我看得还不够明白,我要故意睡着,好让我的梦给我把它更真实、
更明显地提供出来,是同样不合道理的。这样一来,我确切地认识
到,凡是我能用想象的办法来理解的东西,都不属于我对我自己的
认识;认识到,如果要让精神把它的性质认识得十分清楚,那么我
就需要让它不要继续用这种方式来领会,要改弦更张,另走别的路
子。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
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
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当然,如果所有这些
东西都属于我的本性,那就不算少了。可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属
于我的本性呢?难道我不就是差不多什么都怀疑,然而却了解、领
会某些东西,确认和肯定只有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否认一切别的东
西,愿意和希望认识得更多一些,不愿意受骗,甚至有时不由得想
象很多东西,就像由于身体的一些器官的媒介而感觉到很多东西
的那个东西吗?难道所有这一切就没有一件是和确实有我、我确
实存在同样真实的,尽管我总是睡觉,尽管使我存在的那个人用尽
他所有的力量来骗我?难道在这些属性里边就没有一个是能够
同我的思维有分别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我自己分得开的吗?因为
事情本来是如此明显,是我在怀疑,在了解,在希望,以致在这里用
不着增加什么来解释它。并且我当然也有能力去想象;因为即使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我以前曾经假定的那样),即我所想象的
那些东西不是真的,可是这种想象的能力仍然不失其为实在在我
心里,并且做成我思维的一部分。总之,我就是那个在感觉的东
西,也就是说,好像是通过感觉器官接受和认识事物的东西,因
为事实上我看见了光,听到了声音,感到了热。但是有人将对我
说:这些现象是假的,我是在睡觉。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至少我似
乎觉得就看见了,听见了,热了,这总是千真万确的吧;真正来
说,这就是在我心里叫做在感觉的东西,而在正确的意义上,这就
是在思维。从这里我就开始比以前稍微更清楚明白地认识了我是
什么。
可是,当我考虑我的精神是多么软弱,多么不知不觉地趋向于
错误的时候,我不能太奇怪。因为即使我不言不语地在我自己心
里考虑这一切,可是言语却限制了我,我几乎让普通言语的词句引
入错误;因为如果人们把原来的蜡拿给我们,我们说我们看见这就
是那块蜡,而不是我们判断这就是那块蜡,由于它有着同样的颜色29
和同样的形状。从这里,假如不是我偶然从一个窗口看街上过路
的人,在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我看见了一些人,就如同
我说我看见蜡一样,那么我几乎就要断定说:人们认识蜡是用眼睛
看,而不是光用精神去观察。可是我从窗口看见了什么呢?无非
是一些帽子和大衣,而帽子和大衣遮盖下的可能是一些幽灵或者
是一些伪装的人,只用弹簧才能移动。不过我判断这是一些真
实的人,这样,单凭我心里的判断能力我就了解我以为是由我眼
睛看见的东西。
因为,如果由于我看见蜡而断定有蜡,或者蜡存在,那么
由于我看见蜡因此有我,或者我存在这件事当然也就越发明显,因
为,有可能是我所看见的实际上并不是蜡;也有可能是我连看东西
的眼睛都没有;可是,当我看见或者当我想是看见(这是我不再加
以区别的)的时候,这个在思维着的我倒不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不
可能的。同样,如果由于我摸到了蜡而断定它存在,其结果也一
样,即我存在;如果由我的想象使我相信而断定它存在,我也总是
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在这里关于蜡所说的话也可以适用于外在于
我、在我以外的其他一切东西上。
那么,如果说蜡在不仅经过视觉或触觉,同时也经过很多别的
原因而被发现了之后,我对它的概念和认识好像是更加清楚、
更加分明了,那么,我不是应该越发容易、越发明显、越发分明地认
识我自己了吗?因为一切用以认识和领会蜡的本性或别的物
体的本性的理由都更加容易、更加明显地证明我的精神的本
性。除了属于物体的那些东西以外,在精神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能够有助于阐明精神的本性,那些东西就不值得去提了。
可是,我终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原来想要回到的地方;因
为,既然事情现在我已经认识了,真正来说,我们只是通过在我们
心里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过想象,也不是通过感官来领会物体,
而且我们不是由于看见了它,或者我们摸到了它才认识它,而只是
由于我们用思维领会它,那么显然我认识了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比
我的精神更容易认识的东西了。
论上帝及其存在
可是当我考虑有关算学和几何学某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
东西,比如三加二等于五,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不
是至少把它们领会得清清楚楚,确实知道它们是真的吗?当然,假
如从那以后,我认为可以对这些东西怀疑的话,那一定不是由于别
的理由,而只是因我心里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也许是一个什么上
帝,他给了我这样的本性,让我甚至在我觉得是最明显的一些东西
上弄错。但是每当上述关于一个上帝的至高无上的能力这种见解
出现在我的思维里时,我都不得不承认,如果他愿意,他就很容易
使我甚至在我相信认识得非常清楚的东西上弄错。可是反过来,
每当我转向我以为领会得十分清楚的东西上的时候,我是如此地
被这些东西说服,以致我自己不由得说出这样的话:他能怎么骗我
就怎么骗我吧,只要我想我是什么东西,他就决不能使我什么都不
是;或者既然现在我存在这件事是真的,他就决不能使我从来或者
有那么一天没有存在过;他也决不能使三加二之和多于五或少于
五,或者在我看得很清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不能像我所领会的
那个样子。
并且,既然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有个什么上帝是骗子,既然我
还对证明有一个上帝的那些理由进行过考虑,因此仅仅建筑在这
个见解之上的怀疑理由当然是非常轻率的,并且是(姑且这么说)
形而上学的。可是,为了排除这个理由,我应该在一旦机会来到的
时候,检查一下是否有一个上帝;而一旦我找到了有一个上帝,我
也应检查一下他是否是骗子。因为如果不认识这两个事实真相,
我就看不出我能够把任何一件事情当作是可靠的。
在我的各类思维之中,有些是事物的影像。只有在这样一些
思维才真正适合观念这一名称:比如我想起一个人,或者一个怪
物,或者天,或者一个天使,或者上帝本身。除此而外,另外一些思
维有另外的形式,比如我想要,我害怕,我肯定,我否定;我虽然把
某种东西领会为我精神的行动的主体,但是我也用这个行动把某
些东西加到我对于这个东西所具有的观念上;属于这一类思维的
有些叫做意志或情感,另外一些叫做判断。
至于观念,如果只就其本身而不把它们牵涉到别的东西上去,
真正说来,它们不能是假的;因为不管我想象一只山羊或一个怪
物,在我想象上同样都是真实的。
也不要害怕在情感或意志里边会有假的;即使我可以希望一些坏事情,
或者甚至这些事情永远不存在,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我对这些事情的希望不是真的。
这样,就只剩下判断了。在判断里我应该小心谨慎以免弄错。
而在判断里可能出现的重要的和最平常的错误在于我把在我心里
的观念判断为和在我以外的一些东西一样或相似;因为,如果我把
观念仅仅看成是我的思维的某些方式或方法,不想把它们牵涉到
别的什么外界东西上去,它们当然就不会使我有弄错的机会。
在这些观念里边,有些我认为是与我俱生的,有些是外来的,
来自外界的,有些是由我自己做成的和捏造的。因为,我有领会一
般称之为一个东西,或一个真理,或一个思想的功能.我觉得这种
功能不是外来的,而是出自我的本性的;但是,如果我现在听见了
什么声音,看见了太阳,感觉到了热,那么一直到这时候我判断这
些感觉都是从存在于我以外的什么东西发出的;最后,我觉得人
鱼,鹫马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切怪物都是一些虚构和由我的精
神凭空捏造出来的。可是也许我可以相信所有这些观念都是属于
我称之为外来的、来自我以外的这些观念,或者它们都是与我俱生
的,或者它们都是由我做成的;因为我还没有清楚地发现它们的真
正来源。我现在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在有关我觉得来自我以外的
什么对象的那些观念,看看有哪些理由使我不得不相信它们是和
这些对象一样的。
第一个理由是:我觉得这是自然告诉我的;第二个理由是:我
自己体会到这些观念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它们经常不
由我自主而呈现给我,好像现在,不管我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
感觉到了热,而由于这个原因就使我相信热这种感觉或这种观念
是由于一种不同于我的东西,即由于我旁边的火炉的热产生给
我的。除了判断这个外来东西不是把什么别的,而是把它的影像
送出来印到我心里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我认为更合理的了。
现在我必须看一看这些理由是否过硬,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
当我说我觉得这是自然告诉我的,我用自然这一词所指的仅仅是
某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使我相信这个事情,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光
明使我认识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
对于自然的光明使我看到都是真的这件事,我一点都不能怀疑,就
像它刚才使我看到由于我怀疑这件事,我就能够推论出我存在一
样。在辨别真和假上,我没有任何别的功能或能力能够告诉我说
这个自然的光明指给我是真的东西并不是真的,让我能够对于那
种功能或能力和对于自然的光明同样地加以信赖。可是,至于倾
向,我觉得它们对我来说也是自然的,我时常注意到,当问题在于
在对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倾向使我选择恶的时候并不比
使我选择善的时候少;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真和假上,我也并不依
靠倾向的原故。
因而只剩下上帝的观念了,在这个观念里边,必须考虑一下是
否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来源我自己的。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
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
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
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这些优点是这样巨大,这
样卓越,以致我越认真考虑它们,就越不相信我对它们所具有的观
念能够单独地来源于我。因此,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中,必然得出上
帝存在这一结论;因为,虽然实体的观念之在我心里就是由于我是
一个实体,不过我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而我不能有一个无限的实
体的观念,假如不是一个什么真正无限的实体把这个观念放在我
心里的话。
我不应该想象我不是通过一个真正的观念,而仅仅是通过有
限的东西的否定来领会无限的,就像我通过动和光明的否定来理
解静和黑暗那样;因为相反,我明显地看到在无限的实体里边比在
一个有限的实体里边具有更多的实在性,因此我以某种方式在我
心里首先有的是无限的概念而不是有限的概念,也就是说,首先有
的是上帝的概念而不是我自己的概念。因为,假如在我心里我不
是有一个比我的存在体更完满的存在体的观念,不是由于同那个
存在体做了比较我才会看出我的本性的缺陷的话,我怎么可能认
识到我怀疑和我希望,也就是说,我认识到我缺少什么东西,我不
是完满无缺的呢?
不能说这个上帝的观念也许实质上是假的,是我能够从无中
得出它来的,也就是说,因为我有缺陷,所以它可能存在我心里,就
像我以前关于热和冷的观念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的观念时所
说的那样;因为,相反,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它本身
比任何别的观念都含有更多的客观实在性,所以自然没有一个观
念比它更真实,能够更少被人怀疑为错的和假的了。
我说,这个无上完满的、无限的存在体的观念是完全真实的;
因为,虽然也许可以设想这样的一个存在体是不存在的,可是不能
设想它的观念不给我表象任何实在的东西,就像我不久以前关于
冷所说的那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放下别的,只考虑一下具有上帝的这个
观念的我自己,如果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存在。我问:
我是从谁那里得到我的存在呢?也许从我自己,或者从我的父母,
或者从不如上帝完满的什么其他原因;因为不能想象有比上帝更
完满,或者和上帝一样完满的东西。
那么,如果我不依存于其他一切东西,如果我自己是我的存在
的作者,我一定就不怀疑任何东西,我一定就不再有希望,最
后,我一定就不缺少任何完满性;因为,凡是在我心里有什么观
念的东西,我自己都会给我,这样一来我就是上帝了。
当然不应该奇怪,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
里,就如同工匠把标记刻印在他的作品上一样;这个标记也不必一
定和这个作品有所不同。可是,只就上帝创造我这一点来说,非常
可信的是,他是有些按照他的形象产生的我,对这个形象(里面包
含有上帝的观念),我是用我领会我自己的那个功能去领会的,也
就是说,当我对我自己进行反省的时候,我不仅认识到我是一个不
完满、不完全、依存于别人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停地倾向、希望比我
更好、更伟大的东西,而且我同时也认识到我所依存的那个别人,
在他本身里边具有我所希求的、在我心里有其观念的一切伟大的
东西,不是不确定地、仅仅潜在地,而是实际地、现实地、无限地具
有这些东西,而这样一来,他就是上帝。我在这里用来证明上帝存
在的论据,它的全部效果就在于我认识到,假如上帝真不存在,我
的本性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在我心里有一个
上帝的观念;我再说一遍,恰恰是这个上帝,我在我的心里有其观
念,也就是说,他具有所有这些高尚的完满性,对于这些完满性我
们心里尽管有什么轻微的观念,却不能全部理解。他不可能有任
何缺点;凡是标志着什么不完满性的东西,他都没有。
论真理和错误
因为,首先,我看出他(上帝)绝对不能骗我,因为凡是欺骗都含有某
种不完满性;而且即使能够骗人好像标志着什么机智和能力,不
过,想要骗人却无疑地证明是一种缺陷或恶意。因此在上帝里边
不可能有欺骗。
其次,我体验到在我自己的心里有某一种判断能力,
这种能力和我所具有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无疑是我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
而且,因为他不想骗我,所以他肯定没有给我那样的一种判断能力,
让我在正当使用它的时候总是弄错。
因此我认为假如不是从这里得出我永远不会弄错这样的结论的话,
那么对这个真理就再没有可怀疑的了;因为,如果凡是我所有的都是来自上帝的,
如果他没有给我弄错的能力,那么就应该说,我决不应该弄错。
真地,当我单单想到上帝时,我在心里并没发现什么错或假 的原因;
可是,后来,当我回到我自己身上来的时候,经验告诉我,
我还是会犯无数错误的而在仔细追寻这些错误的原因时,
我注意到在我的思维中不仅出现一个实在的、肯定的上帝观念,
或者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观念,同时,姑且这样说,也出现一个
否定的、“无”的观念,也就是说,与各种类型的完满性完全相反的观念;
而我好像就是介乎上帝与无之间的,也就是说,我被放在至上存在体和非有在体之间,
这使得我,就我是由一个至上存在体产生的而言,
在我心里实在说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导我到错误上去;
但是,如果我把我看成是以某种方式分享了无或非存在体,
也就是说,由于我自己并不是至上存在体,我处于一种无限缺陷的状态中,
因此我不必奇怪我是会弄错的。
这样一来,我认识到,错误,就其作为错误而言,并不取决于上帝的什么实在的东西,
而仅仅是一种缺陷,从而对于犯错误来说,我不需要有上帝专门为这个目的而给我什么能力,
而是我所以有时弄错是由于上帝给了我去分辨真和假的能力对我来说并不是无限的。
虽然如此,我还不完全满足;因为,错误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否
定,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缺陷或者缺少我不应该有的什么完满
性,而是缺少我似乎应该具有的什么认识。而且,在考虑上帝的性
质时,我认为,如果说他给了我某种不完满的,也就是说,缺少什么
必不可少的完满性的功能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匠越是精
巧熟练,从他的手里做出来的活计就越是完满无缺的这件事如果
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由一切事物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所产
生的东西,有哪一种在其各个部分上不是完满、完全精巧的呢?
当然,毫无疑问,上帝没有能把我创造得永远不能弄错;同时的确
他也总是愿意要最好的东西。那么弄错比不弄错对于我更有好处吗?
而且,自从我故意怀疑一切事物以来,虽然我仅仅肯定地认识了我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
可是自从我认出了上帝的无限潜能以来,我就不能否认他也产生了其他
很多东西,或者至少它能够产生那些东西,因而我也不能否认我存
在并且被放在世界里,作为一切存在的东西的整体的一个部分。
从所有这些,我认识到,我错误的原因既不是意志的能力本身
(它是我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的),因为它本性是非常广泛、非常完
满的;也不是理解的能力或领会的能力,因为,既然我用上帝所给
我的这个能力来领会,那么毫无疑问,凡是我所领会的,我都是实
事求是地去领会,我不可能由于这个原故弄错。那么我的错误是
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这里产生的,即,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多、
广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
理解不到的东西上去,意志对这些东西既然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
很容易陷于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来选
取了。这就使我弄错并且犯了罪。
因为事实上,假如说上帝并没有给我自由让我对于在他没有
在我的理智里放进一种清楚、明白的认识的某些事物上去下判断
或者不去下判断,这也不是在上帝方面的一种不完满,而无疑地是
在我方面的不完满,是我没有使用好这个自由,因为是我在我领会
得不清楚和糊里糊涂的一些事物上卤莽地下了判断。
可是,我看得出,虽然我一直是自由的,并且具有少量的认识,
也就是说,上帝在把一种清楚、明白的智慧给了我的理智,使我对
于一切事物用不着我加以丝毫考虑时,或者他仅仅把我在领会得
不清楚、不明白时永远不去对任何事物下判断这样的一个决心深
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永远忘不了它,那么他本来是很容易使
我决不弄错的。而且我看出来,只要我把我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
的,就好像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似的,如果上帝把我造成为永远不弄
错,那么我就会比我现在完满得多。可是我不能因此就否认在某
种意义上,宇宙的某几个部分难免错误比一切部分都错误,会有
更大的完满性。而且上帝在把我投入世界中时,如果没有想把
我放在最局贵、最完满的东西的行列里去,我也没有任何权利去埋
怨。甚至我有理由满意:如果他没有给我由于我前面说过的第一
个办法而不犯错误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我对于我所能够考
虑的一切事物的一种清楚、明白的认识),他至少在我的能力里边
留下了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下定决心在我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弄
清楚以前无论如何不去下判断。因为,虽然我看到在我的本性
中的这种缺陷,即我不能不断地把我的精神连到一个同一的思
想上,可是我仍然由于一种专心一致的并且时常是反复的沉思,能
够把它强烈地印到我的记忆中,使我每次在需要它的时候不能不
想起它,并且由于这种办法能够得到不致犯错误的习惯。而且,由
于人的最大的、主要的完满性就在于此,我认为我从这个“沉思”
里获益不浅,因为我发现了虚假和错误的原因。
此外,今天我不但知道了必须避免什么才能不致犯错误,而且
也知道了我必须做什么才能认识真理。因为,如果我把我的注意
力充分地放在凡是我领会得完满的事物上,如果我把这些事物从
其余的、我所理解得糊里糊涂的事物中分别出来,我当然就会认
识真理。这就是我今后将要认真加以注意的。
论物质性东西的本质;再论上帝及其存在
当我这样一般地加以考虑的时候,我不仅清楚地认识了这些
东西,而且在我稍微加以注意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有关数目、形状、
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无数特点,这些特点的真实性不但表现得非
常明显,而且和我的本性竟那么相合,以致当我开始发现这些特点
时,我似乎并没有知道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想起了我从前已经知道
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发现了一些早已在我心里的东西,尽管我以
前没有想到它们。
目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我心里有某些东西的无数
观念,虽然这些东西也许在我的思维之外没有什么存在性,可是不
能就认为它们是纯粹的无;而且,虽然我可以想到它们或者不想到
它们,它们并不是我凭空捏造的,而是有它们真实、不变的本性的。
举例来说,当我想到一个三角形时,即使在我的思维以外也许世界
上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存在这样的一个形状,也许从来没有过,可是
毕竟这个形状的某一种确定的性质或形式或本质还是有的,它是
不变的、永恒的,不是我凭空捏造的,也决不取决于我的精神,就像
我们能够从推证出这个三角形的各种特性这件事所表现的那样
(比如它的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最大的角对最大的边,以及诸如
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尽管在我从前第一次想到一个三角形时我
绝对没有想到过),那么现在我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不管我
愿意不愿意,它们都是三角形之内的东西,因而不能说这是我凭空
捏造的。
可是,虽然事实上我不能领会一个不带存在性的上帝,也不能
领会一个不带谷的山,不过,既然仅仅由于我领会一个带谷的山不
能因此就说世界上有山,同样,虽然我领会带存在性的上帝也不并
不能因此就说有一个上帝存在,因为我的思维并不给事物强加
什么必然性;而且,尽管并没有什么带翅膀的马,而我却想出来一
个带翅膀的马,同样,尽管并没有什么上帝存在,我也许能够给上
帝加上存在性。绝对不是这样。这个反驳的外表掩盖下的诡辩就
在于此。因为,从我不能领会一个不带谷的山这一事实,不能得出
世界上根本没有山,也根本没有谷这个结论,而只能得出山和谷,
不管它们有也罢,没有也罢,彼此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分的;相反,
仅仅由于我不能把上帝领会成不带存在性,所以存在性和上帝
是不可分的,所以上帝是存在的。不是因为我把事物想成怎么样
事物就怎么样,并且把什么必然性强加给事物;而是反过来,是
因为事物本身的必然性,即上帝的存在性,决定我的思维去这样领
会它。因为我可以随便想象一个马不带翅膀或者带翅膀,可是
我并不能随便领会一个没有存在性的上帝,也就是说,我不能随便
领会一个缺少一种至上完满性的至上完满的存在体。
举例来说,当我考虑三角形的性质时,我显然知道(我在几
何学方面有些内行)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而且当我把我的
思维运用到证明它的时候,我不可能不相信这一点;可是,只要我
的注意力稍微离开证明,虽然我记得我是清清楚楚地理解了它的85
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不过假如我不知道有一个上帝,我还是很可
能会怀疑它的真实性的,因为我可以说服我自己:大自然使我生来
就很容易能够在即使我以为理解得最明显、最可靠的东西上弄错,
主要因为我记得经常把很多事物认为是真实、可靠的,而以后又有
别的理由使我把这些事物判断成是绝对错误的。
可是当我认识到有一个上帝之后,同时我也认识到一切事物
都取决于他,而他并不是骗子,从而我断定凡是我领会得楚楚、分
明的事物都不能不是真的,虽然我不再去想我是根据什么理由把
一切事物断定为真实的,只要我记得我是把它清楚、分明地理解
了,就不能给我提出任何相反的理由使我再去怀疑它,这样我对这
个事物就有了一种真实、可靠的知识,这个知识也就推广到我记得
以前曾经证明过的其他一切事物,比如推广到几何学的真理以及
其他类似的东西上去。因为,为什么反驳我,迫使我去怀疑它们
呢?是因为我的本性如此,使我老是弄错?可是我已经知道在我
对于认识得清楚的那些理由时所下的判断里,我是不会弄错的。
是因为我从前把很多东西认为是真实、可靠的,而以后我认识到它
们是错的吗?可是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我认识得清楚、明白
的,而且那时我还不知道使我确实认识真理的这条规律,我是由于
一些理由相信了它们,而以后我看出那些理由还不如我当时想象
的那么有说服力。还能再有什么可反驳我的吗?是因为也许我睡
着了(就像我以前反驳过我自己的那样),或者是因为我现在的这
些想法并不比我们想象是睡着了时做的梦一样地不真实呢?可
是,即使我睡着了,凡是明明白白出现在我心里的都是绝对真实
的。因此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切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取
决于对于真实的上帝这个唯一的认识,因而在我认识上帝以前,我
是不能完满知道其他任何事物的。而现在我既然认识了上帝,我
就有办法取得关于无穷无尽的事物的完满知识,不仅取得上帝之
内的那些东西的知识,同时也取得属于物体性质的那些东西的知
识,因为物体性质可以用做几何学家们推证的对象。几何学家们
是不管这个对象的存在性的。
论物质性东西的存在;论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
如果我要想一个千边形,我当然领会这是一个由一千个边组成的形状,
和我领会一个三角形是仅仅由三个边组成的形状同样容易,但是我却不能像我想
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边那样想一个千边形的一千个边,也不能(姑且
这样说)用我精神的眼睛把一千个边看成是出现在我面前的。而
且虽然当我想物体性的东西时,我总习惯于使用我的想象,于是在
我领会一个千边形时,我模模糊糊地表象出一个什么形状;不过这
个形状显然并不是一个千边形,因为这个形状跟我想一个万边形
或别的一个有非常多的边的形状时所表象出来的形状没有什么不
同,而且决不能用它来发现千边形和别的多边形之间的差别。
此外我还看出,在我心里这种想象的能力,就其有别于领会的
能力来说,对我的本性或对我的本质,也就是说,对我的精神的本
质,决不是必要的;因为,即使我没有这种想象的能力,无疑我仍然
会和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从而可以断言,它并不取决于我的
精神,而是取决于不同于我的精神的别的什么东西。而且我很容
易领会到,如果说有什么物体存在,而我的精神和它连结得非常紧
密,以致它愿意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就可以考虑它,那么精神就
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想象物体性的东西了。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与
纯粹理智之不同仅在于:在领会时,精神以某种方式转向其自身,
并且考虑在其自身里的某一个观念;而在想象时,它转向物体,并
且在物体上考虑某种符合精神本身形成的或者通过感官得来的观
念。我说,我很容易领会到,如果真有物体,想象是能够这样做成
的,而且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别的办法来说明想象是怎么做成的,所
以我就猜测或许物体是存在的;可是,这只能说是“或许”;尽管我
仔细检查一切东西,我仍然看不出来从我的想象里的这种关于物
体的本性的清楚观念里能够得出什么物体存在的必然性的任何证
明来。
可是,除了作为几何学的对象的这种物体性质以外,我习惯于
想象很多别的东西,像颜色、声音、滋味、疼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虽然不那么清楚。而且因为通过感官我就更好地觉察这些东西,
通过感官和记忆的媒介,这些东西就好像是达到我的想象,所以我
认为,为了更方便地检查它们,我觉得也应该同时检查一下什么是
感觉,看看从我称之为感觉的这种思维方式接受到我的心里来的
这些观念里,我是不是能得出来什么可靠的证据来证明物体性的
东西的存在。
因此首先我感觉到我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以及组成我
看成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个肉体的其余一切部分。
此外,我感觉到这个肉体是处于其他很多物体之间的,从这些物体
上它有能力感到不同种类的舒适和不舒适。我通过某一种愉快或
满足欲望的感觉而看出舒适,通过某一种痛苦的感觉而看出不舒
适。在愉快和痛苦之外,我还在我的内部感觉到饿、渴以及其他类
似的饮食之欲,我也感觉到对于喜、哀、怒,以及其他类似的情绪的
某些物体性的倾向。在外部,除了物体的广延、形状、运动之外,我
还在物体里看出软硬、干湿以及落于触觉的其他一切特性。此外,
我在那里看出明暗、颜色、气味、滋味和声音,而多种多样的明暗、
颜色、气味、滋味和声音给了我办法,使我把天、地、海以及总而言
之其他一切物体都彼此分辨出来。
而且因为我通过感官得来的那些观念,比起我沉思时所能虚
构的任何观念来,或者比起我认为印在我的记忆里的任何观念来
都要生动得多,明显得多,甚至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得清楚得
多,看来它们不能是从我心里产生的,所以它们必然是由一些别的
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引起的。既然除了那些观念给我的认识以外,
我对那些东西什么认识都没有,那么除非那些东西是和它们所引
起的观念一样,此外就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来到我的心里了。
因为,我也记得我使用的是感官而不是理性,并且我认识到我
自己做的那些观念不如我通过感官得来的观念那么明确,何况那
些观念经常也是我通过感官得来的观念之中的一部分构成的,所
以我很容易相信在我心里我决没有什么观念不是从前通过我的感
官得来的。
可是,当我检查为什么从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痛苦之感就引起
心里的悲伤,愉快之感就引起快乐,或者为什么这种我不知道是什
么的胃的刺激(我把它叫做饿)让我们想要吃东西,喉咙发干让我
想要喝水,以及其他等情况,这除了这是自然这样告诉我的,我找
不出别的道理来;因为在胃的刺激和想要吃东西之间,以及引起痛
苦的东西的感觉和这个感觉引起悲伤思想之间,没有(至少是我理
解不了的)任何关系。同样道理,我好像是从自然那里知道了我判
断的有关我的感官对象的其他一切东西;因为我看到我有习惯在
这些对象上所做的那些判断,它们是在我有工夫掂算和考虑能够
使我做出这样的判断以前就形成了的。
可是以后,有许多经验逐渐破坏了我以前加给我的感官的全
部信任。因为我多次看到,有些塔我远看好像是圆的,而我近看却
是方的;耸立在塔顶上的巨大塑像从塔底下看却是小小的塑像;这
样,在其他无数场合中,我都看出根据外部感官所下的判断是有错
误的。不仅外部感官,就连根据内部感官所下的判断也一样。因
为,有什么东西比痛苦更亲密、更内部的吗?可是从前有些把胳臂
或腿截去了的人对我说有时他们还感觉到已经截去了的那部分
疼,这使我有理由想到,虽然我感觉到我某一个肢体疼,我也不能
肯定它疼。
首先,因为我知道凡是我清楚、分明地领会的东西都能就像我
所领会的那样是上帝产生的,所以只要我能清楚、分明地领会一个
东西而不牵涉到别的东西,就足以确定这一个东西是跟那一个东
西有分别或不同的,因为它们可以分开放置,至少由上帝的全能把
它们分开放置;至于什么力量把它们分开,使我把它们断定为不同
的东西,这倒没有关系。从而,就是因为我确实认识到我存在,同
时除了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
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所以我确实有把握断言我的
本质就在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个实体,这
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而且,虽然也许(或者不如说
的确,像我将要说的那样)我有一个肉体,我和它非常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不过,因为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楚、分明的观念,即
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没有广延,而另一方面,我对于肉体有
一个分明的观念,即它只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维,所以肯
定的是:这个我,也就是说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
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
存在。
可是,既然上帝不是骗子,那么显然他不会自己直接地,也不会通过什么造物的媒介
(在这个造物里并不是形式地,而仅仅是卓越地包含观念的实在性)
把这些东西的观念送给我。
因为,既然没 有给我任何功能来认识事情是这样的,反而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倾向性
使我相信它们是物体性的东西送给我的,或者来自物体性的东西的,
那么如果事实上这些观念不是来自或产生于物体性的东西而是来自成产生于别的原因,
我就看不出怎么能辩解它不是一个骗局。因此必须承认有物体性的东西存在。
首先,毫无疑问,凡是自然告诉我的都含有某种真实性。因为
自然,一般来说,我指的不是别的,而是上帝本身,或者上帝在各造
物里所建立的秩序和安排说的。至于我的个别自然〔本性〕,我
不是指别的东西,而是指上帝所给我的一切东西的总和说的。
可是没有再比这个自然告诉我的更明白、更显著的了,那就是
我有一个肉体,当我感觉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舒服;当我感觉饿或
渴的时候,它就需要吃或喝,等等。因此我决不怀疑在这上面有没
有真实性。
自然也用疼、饿、渴等等感觉告诉我,我不仅住在我的肉体里,
就像一个舵手住在他的船上一样,而且除此而外,我和它非常紧密
地连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像一个整体一样地同它结合在一起。
因为,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当我的肉体受了伤的时候,我,这个仅仅
是一个在思维的我,就不会因此感觉到疼,而只会用理智去知觉这
个伤,就如同一个舵手用视觉去察看是不是在他的船上有什么东
西坏了一样;当我的肉体需要饮食的时候,我就会直截了当地认识
了这件事,用不着饥渴的模糊感觉告诉我。因为事实上,所有这些
饥、渴、疼等等感觉不过是思维的某些模糊方式,它们是来自并且
取决于精神和肉体的联合,就像混合起来一样。
比如,星星给我眼睛的印象虽然并不比蜡烛的小小火焰给
我的印象大,可是在我心里却决没有一种实在的或自然的功能使
我相信星星并不比蜡烛的火焰大,不过我自幼年起就一直这样判
断的,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在我挨近火的时候虽然我感觉到热,
甚至在我挨得太近的时候,我感觉到疼,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
相信火里有什么跟热一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跟疼一样的东西,我
不过是有理由相信火里有什么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吧,它给
我刺激起来热或疼的感觉。
同样,在有些空间里虽然我找不出什么能刺激和触动我的感
官的东西,可是我不应该因此就断言这些空间里绝对没有物体。
不过我看出,不管是在这方面或者在其他许多类似的事情方面,我
经常是把自然的秩序给弄坏、弄乱了,这是因为,感官的这些感觉
或知觉之被放在我里边仅仅是为了警告我的精神什么东西对总和
体(精神是这个总和体的一部分)是有好处的或者有坏处的,到这
里为止,它们本来是相当清楚、相当分明的,可是我却把它们当成
好像是非常可靠的、我可以由之而直接认识在我之外的规律一样
来使用了,而关于物体的本质或本性,它们能告诉我的却都是非常
不清楚的。
可是我前面已经检查得足够充分了,尽管上帝是至善的,
我有时在这一类的判断里仍会有错。在有关自然告诉我应该趋就或躲避的东西上,
在有关自然放在我里边的内部感觉上,到现在还出现困难;因为我有时看出错误,
这样我就直接被我的自然所欺骗。举例来说,肉里放上了毒药而肉的滋味很香,
可以引诱我去吃毒药, 这样一来我就受了骗。不错,在这方面当然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它仅仅让我吃滋味很香的肉,并没有让我吃它所不知道的毒药,
因而我只能由这件事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的自然不能完全、普遍认识一切事物,
这当然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人既然是一种有限的自然,
就只能具有有限完满性的认识。
不过我们经常也在我们直接由自然得到的那些东西上弄错,
就像有时病人希望吃喝可能对他们有害的东西一样。人们在这上面会说,
引起他们弄错的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本性〕坏了。可是问题不在这里,
因为一个病人也和健康的人一样,真正是上帝的造物,
所以他和别人同样不愿意上帝的善心使他有一个骗人的自然〔本性〕,
就像一个由轮子和摆装成的钟表一样,当这个钟表做得不好,
不能完全满足钟表工匠的希望来指好时间时,也是同样准确地遵守自然的一切规律的;
同样情况,如果我把人的肉体看成是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
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一样,即使里边没有精神,
也并不妨碍它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动作,这时它不是由意志指导,
因而也不是由精神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器官的安排来动作。
因此我很容易认识到,既然这个身体,比如说,是水肿病患者,
他自然就由于喉咙发干感到难受,喉咙发干习惯地给精神以渴的感觉,
因而趋向于引动他的神经和其他部分让他要求喝水,这样一来就增加他的病痛,
害了他自己,这和他没病时由于喉咙发干而喝水以应身体的需要是同样自然的。
虽然我看到一个钟表被造这个钟表的人指定了它的用途,我可以说,
如果这个钟表走得不准,那是因为它违反了它的自然〔本性〕,
这和我把人体这架机器看成是上帝做成的,使它在它里边有它应有的一切运动,
虽然我有理由想,如果它的喉咙发干,没有按照它的自然〔体性〕的秩序办事,
喝了有害于保持它的健康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我认识到,
用后一种方式去解释自然〔本性〕是和用前一种方式解释自然〔本性〕很不相同。
因为后一种方式不是一种单纯的称号问题,它完全取决于我的思维,
是我的思维把一个病人和一座做坏了的钟表拿来
跟我关于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做好了的钟表的观念相比较,
而且它决不意味着任何存在于它所指的东西里的东西;相反,
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自然〔本性〕,我是指某种真正存在于那些东西里的东西,
从而它并不是没有真实性的。
可是,从一个水肿病患者的身体来看,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外部
的称号问题,因为人们说在不需要喝水的情况下,它的喉咙仍然发
干,这是因为它的自然〔本性〕坏了。虽然如此,可是从整个的总和
来看,即从精神或灵魂和肉体的结合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称
号问题,实际是一个自然〔本性〕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于它口渴,而
喝水对它是非常有害的。这样一来,还有待于去检查的就是,像这
样的人的自然〔本性〕既然是虚伪的、骗人的,上帝的善心为什么不
去阻止它。
举例来说,在一条完全抻开的绳子甲、乙、丙、丁四个部分上,如果抻动末一部分
丁,那么第一部分甲就动起来,它动的方式和抻动中间的乙部分或
者丙部分而末一部分丁保持不动的情况一样。和这个情况相同的
是,当我觉得脚上疼的时候,物理学告诉我,这个感觉是通过分布
在脚上的神经传来的,这些神经就像绳子一样从脚上一直通到大
脑里,当它们在脚上被抻动的时候,同时也抻动了大脑里边这些神
经的起点和终点的那个地方,并且在那里刺激起来为了使精神感
觉疼而制定的某一种运动,就好像疼是在脚上似的。可是因为这
些神经要从脚上通到大脑里,就一定经过腿、臀部、腰部、背和颈,
所以也有这样的可能,即虽然它们在脚上的末端并没有被抻动,而
仅仅抻动它们经过腰或颈的某些部分,也会在大脑里刺激起一些
和脚上受伤所接到的同样运动,然后精神也将必然觉得脚上疼,就
好像脚上受了伤似的。我们的感官的其他各种知觉,情况也应该
是这样的。
从以上这些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有上帝的至善,人的自然
〔本性〕,就人是由精神和肉体组合而成的来说,有时不能不是虚伪
的、骗人的。
因为如果有什么原因不是在脚上,而是从脚一直到大脑抻起
来的神经的某一个部分上,或者甚至在大脑里,刺激起来通常和脚
不舒服时所刺激起来的同样运动,那么人们将感觉到疼,就和疼是
在脚上一模一样,感官就自然地要受骗了;因为既然在大脑里的一
个同样运动只能在精神里引起一个同样的感觉,而这个感觉是脚
受伤了的一个原因所刺激比在别处的原因所刺激的时候多得多,
那么这个运动把脚疼①而不是什么别的部分疼带给精神,这样说
总算是更合理一些吧。而且喉咙发干不是像平常那样总是由于喝
水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必要的原因,而是有时由于什么完全相反的
原因,就像患水肿病人所遭遇的那种情况,即使是这样,喉咙发干
在这地方骗人也总比相反地当身体没有不舒服时骗人要好得多。
其他情况也一样。
当然,这个考虑不仅在认识到我的自然〔本性〕可能犯的各种
错误上对我有好处,同时在更容易避免错误或者改正错误上对我
也很有好处。因为,知道了在有关身体的合适或不合适的东西时,
我的各个感官告诉我的多半是真的而不是假的,它们差不多总是
用它们之中几个来检查同一的东西以便为我服务,而且,除此之
外,它们还能利用我的记忆把当前的一些认识连接到过去的一些
认识上去,并且还能利用我的理智,因为我的理智已经发现了我的
各种错误的一切原因,那么从今以后我就不必害怕我的感官最经
常告诉我的那些东西是假的了。而且我应该把我这几天的一切怀
疑都抛弃掉,把它们都当作是言过其实、荒谬绝伦的东西,特别是
把有关我过去不能把醒和梦分别开来的那种非常普遍不肯定的态
度抛弃掉,因为我现在在这上面看出一种非常显著的区别,这个区
别在于我们的记忆决不能像它习惯于把我们醒着时所遇到的那些
事情连接起来那样,把我们的各种梦互相连接起来,把它们跟我们
生活的连续性连接起来。而且事实上,假如有人在我醒着时突然
出现在我面前又突然不见了,就像我在睡着时所见到的影像那样,
使我看不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看不出他是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么我就把他看成是在我大脑里形成的一个怪影或者一个幽灵,
和我在睡着时在大脑里形成的那些怪影或者幽灵一样,而不会把
他看成是一个真人,这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当我知觉到一
些东西,我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在什么
地方,它们出现在我面前的时间,并且我能把我对它们产生的感觉
毫无间断地同我生活的其余部分连接起来,那么我就完全可以肯
定我是在醒着的时候而不是梦中知觉到它们。而且,如果在唤起
我所有的感官、我的记忆和我的理智去检查这些东西之后,这些东
西之中的任何一个告诉我的都没有任何东西跟其余的那些所告诉
我的不一致,那么我就决不应该怀疑这些东西的真实性。因为,从
上帝不是骗子这件事得出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在这上面没有受骗。
然而,由于事情的必然性经常迫使我们在我们得出时间在把
这些事情加以非常仔细的检查之前去决定,那么就必须承认人生
是有可能经常在那些个别的事情上犯错误的;并且最后,必须承认
我们的自然〔本性〕存在着缺陷和弱点。
著者对第一组反驳的答辩
我考虑我父亲也是来自我的祖先;而且,如果看到也在追寻我的父亲的父亲上
我不能把这种进程继续到无限,为了结束这种追寻,我断言有一个
第一原因。再说,我没有仅仅追寻我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就我是
一个在思维着的东西而言,而是我主要地、恰恰是就我是一个在思
维着东西而追寻这种原因,这个在思维着的东西,在许多别的思想
之间,认出了在我心里存着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观念;因为,
我的论证的全部力量就是取决于这里的。首先,因为这个观念使
我认识上帝是什么,至少是按照我所能认识他的那种程度;而且,
按照真正的逻辑的规律,决不要问什么东西是否存在,如果首先不
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其次,因为就是这个观念给了我机会去检查
我是由我自己还是由别人而存在的,也给了我机会认出我的缺点。
最后,就是这个观念,他教导我不仅我的存在有一个原因,而更多
的是这个原因含有各种各样的完满性,从而这个原因就是上帝。
最后,我没有说过一个东西不可能是它自己的动力因;因为,虽然
人们把动力的意义限制在与其结果不相同或者在时间上在其结果
之先的那些原因上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它好
像不应该这样限制它,一方面因为那会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
为谁不知道同一的东西不断与其自身不同、也不能在时间上先在
于它自身?另一方面也因为自然的光明并没有告诉我们动力因的
本性是时间上在它的结果之先。因为,相反,真正说来,它既没有
动力因的名称,也没有动力因的性质,除非是它产生它的结果,从
而它并不是在结果之先。不过,自然的光明当然告诉我们没有任
何东西是不许问它为什么存在,或者不能追寻它的动力因的,或
者,假如它没有动力因,那么问它为什么不需要动力因。因此,如
果我想任何东西以某种方式对它自己的关系就是动力因对它的结
果的关系,远不是从这里我就想要得出结论说有一个第一原因,相
反,从人们称之为第一的这个原因本身,我再继续追寻原因,这样
我就永远不会达到一个第一的原因。可是当然,我坦率地承认能
够有个什么东西,在这个东西里边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如此地
强大、如此地不能穷竭,以致它决不需要任何帮助而存在,并且它
现在也不需要任何帮助而被保存,这样它在某种方式上就是它自
己的原因;我领会上帝就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我过去是永恒存在
的,因为在我之先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看到时间的各个部分是彼此
分开的,这样一来,从我现在存在并不说明我以后还应该存在,如
果,姑且这样说,我不是每时每刻都重新被什么原因创造的话,我
就毫无困难地把这个原因称之为动力因,它不断地用这种方式创
造我,也就是说它保存我。这样一来,虽然上帝过去永远存在,可
是,因为事实上是他自己保存他自己,所以他被说成并且叫做自己
是自己的原因,这似乎是相当正确的。(虽然如此,必须指出,在这
里我的意思并不是谈由动力因的任何一种实在的、肯定的影响做
成的保存,我仅仅是谈上帝的本质是这样的,即他不可能不是永远
存在的。)
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东西能够被认识;
不过,这是一个存在于事实上同时也存在于理智中的东
西,它比仅仅存在于理智中的东西更伟大,所以当人们懂得并且理
解上帝这个名称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人们理解上帝存在于事实上
同时也存在于理智中。在这里有一个形式上的明显错误;因为人
们只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当人们懂得并且理解上帝这个名
称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人们理解的是它意味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
存在于事实上同时也存在于理智中;而被一个词句所意味的东西
并不因此就是真的。可是我的论据是:我们所清楚、分明地领会为
属于什么东西的常住不变的、真正的本性,或本质,或形式的事物,
可以真正地能够被说成或被肯定是属于这个事物的;可是,在我们
足够仔细地追究上帝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清楚、明白地领会他之存
在是属于他的真正的、常住不变的本性的,所以我们能够真正地肯
定他是存在的;或至少这个结论是合法的。不过这个大前提不能
否定,因为大家以前已经同意了,即:凡是我们清楚、分明地理解或
领会的东西都是真的。
著者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
如果有人否认他们具有精神和物体的清楚的观念,我只好请
他们把包含在我的第二个沉思里的东西足够仔细地考虑一下,只
好指出,他们认为大脑的各部分有助于精神去形成我们的思维,这
个意见没有任何正面的理由,这种意见不过是由于他们从未体验
过脱离肉体,他们经常是在他们的活动上受肉体的拖累,这就和假
如有人自从童年起脚上就带上铁镣,他会认为铁镣是他的身体的
一个部分,走路没有它就不行是一样的。
第二点,当你们说我们在我们本身里找不到足以做成上帝的
观念的根据时,你们并没有说出同我的意见相反的东西;因为在第
三个沉思的末尾我自己用明确的词句说:这个观念是与我俱生的,
它不是来自别处,只是来自我自己。我也承认我们可以做成它,尽
管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至上的存在体,而不是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
至上的存在体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相反,我曾说过,我的论据的
全部力量就在于:如果我没有被上帝创造,那么做成这个观念的功
能就不可能在我心里。
你关于苍蝇、植物等等所说的话也决不能证明某种程度的完
满性可以在结果里而在从前并不在它的原因里。因为,要么肯定
是在动物里没有完满性,因为动物和无生物一样没有理性,要么,
如果它有什么完满性,这种完满性是从别处来到它们那里的,太
阳、雨水和土并不是这些动物的全部原因。如果有谁仅仅由于他
不认识有助于一个苍蝇出生的原因并且有着和在一个苍蝇里的一
样多的程度的完满性,而却不确知除了他认识的那些完满性之外
还有别的一些完满性,如果这个人从这里找到机会来怀疑一件(就
像我不久将要大量说的那样)由于自然的光明而明显起来的东西,
那会是一件十分不合道理的事。
你们说在我们心中的上帝的观念不过是一个理性的存在体这
话,我也认为一点也反对不着我。因为,如果一个理性的存在体指
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那就不对;只有如果凡是理智的活动都被
当做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都当做由理性出来的存在体,那才是
对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个世界的全部也可以称之为一个上帝理
性的存在体,也就是说,由上帝的理智的一个简单的行为创造的一
个存在体。我已经在几个地方充分说明过,我仅仅谈这个上帝的
观念的完满性或客观实在性,这种完满性或客观实在性也同样要
求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它里边事实上包含全部只是客观地包含
或通过表象包含的东西,这和某一个工匠所有的一个非常巧妙的
机器的观念中所包含的那种客观的或表象的技巧是一样的。
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
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他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
的灵感看出它来的。从以下的事实看,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他是
从一种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他就要事先认识这个大前提:凡是在
思维的东西都存在。然而,相反,这是由于他自己感觉到如果他不
存在他就不能思维这件事告诉他的。因为,由个别的认识做成一
般的命题,这是我们精神的本性。
一个无神论者能够清楚地认识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
这我并不否认;不过我认为他的认识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因为
凡是可以怀疑的认识都不能叫做知识;既然人们假定他是一个无
神论者,我以前已经指出过,他不能肯定在他认为非常明显的事情
上没有弄错;尽管这种怀疑他没有想到,但是如果他检查一下,或
者如果别人向他提出,他仍然可以怀疑,并且,如果他不承认一个
上帝,他就永远不能摆脱有怀疑的危险。
第四点,当我说上帝既不能撒谎,也不是骗子的时候,我认为
我和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一切神学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你们
所提出的全部相反的意见都不比下面的事实更有说服力,即在否
认了上帝生了气或者他受灵魂的其他激情的支配之后,你们反对
我《圣经》上的有些地方,在那里似乎是把人类的某些激情加给了
上帝。
因为人人都充分认识《圣经》上谈到上帝时一般所使用的方式
(这些方式是合乎一般人的能力的,它们包含着某种真理,不过这
个真理只关系到人)和表示一种更简单、更纯粹的真理(这种真理
在性质上并不改变,虽然它不关系到人)的那些方式(关于这些方
式,每个人都在进行哲学思考时使用它们,我在我的《沉思集》也不
得不主要地使用这些方式,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假定我认识
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考虑到我是肉体和精神的组合,我仅仅考虑
到我是一个精神)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然而我不愿意责备那些人,他们说上帝用他的先知的口说出
什么口头上的谎话,就像医生们在为了给他们的病人治病而骗他
们所使用谎话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一般在欺骗里边的全部恶意都
不算数;但是,尤有甚者,有时我们看到我们真地上了上帝所给我
们的天然本能的当,就像当一个水肿病人口渴时那样;因为那时他
真是受上帝为了保存他的肉体所给他的天性促使他喝水,尽管这
种天性骗了他,因为喝水对他是有害的;不过我在第六个沉思里解
释过这怎么可以与上帝的善和真相提并论。
当然,土耳其人和其他一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当他们不接受基
督教时,并不是因为不愿信仰模糊不清的东西由于这些东西是模
糊不清的原故而犯罪;他们犯罪是由于他们拒绝从内部告知他们
的那种圣宠,或者由于他们在别的事情上犯了罪,不配享受这种恩
宠。我敢说,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他被排除于享受任何超自然的
圣宠之外,并且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些基督教徒所信仰的那些东西
是上帝所启示的,可是,由于受到某些错误推理的引导,他也会信
仰和我们所信仰的同样的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是模糊
不清的;虽然如此,这个不信基督教的人并不会因此就是基督教的
信徒,而不如说他之所以犯罪是由于他没有很好地使用他的理性。
按几何学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区别的理由
第一,我要求读者们考虑一下,直到现在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感
官的那些理由都是非常软弱无力的,他们一向依靠感官所下的判
断都是非常靠不住的。我要求他们长时间地、反复地加以考虑,使
他们最后习惯于不再去那么坚强地相信他们的感官时为止;因为
我认为这对于能够认识形而上学的东西的真理是必要的。形而上
学的东西是不依靠感官的。
第二,我要求他们考虑一下他们本身的精神以及精神的全部
属性,这些属性是他们将要看出是决不能有所怀疑的,虽然他们把
他们一向通过感官得来的东西都假定为完全是错误的。我要求他
们对这一点要不断地考虑下去,直到他们首先习惯于清楚地领会
并且相信它比一切物体性的东西都更容易认识时为止。
第三,我要求他们专心研究一下不需要证明就能认识的、其中
每一个的概念都能在它自身中找到的那些命题。例如:一个东西
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无”不能是任何东西的动力因,以及诸如
此类的东西。我要求他们运用自然给他们的这种理智的明白性,
这种明白性由于感官的干扰,经常被弄得模糊起来。我说,我要求
他们运用完全纯粹的、从他们的成见中摆脱出来的这种理智的明
白性,因为,通过这种办法,后面将要谈到的公理的真实性对他们
就会显得十分明白了。
第四,我要求他们对那样的一些性质〔或本性(nature)的观念加以研究,
在那些观念里边含有许多属性的一个总和,比如三角
形的性质,四边形或别的什么形状的性质;比如精神的性质,肉体
的性质,以及再加上上帝或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性质。他们
要注意,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相信所有那些东西都是在观念里边,
我们清清楚楚地领会它们是包含在那里的。举例来说,由于在直
线三角形的性质里,包含着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在物体或一个有
广延的东西的性质里包含着可分解性(因为凡是有广延性的东西
不管它有多么小,我们都把它领会为不是不可分割的,至少是可以
用思维来分割),所以说一切直线三角形三角之和都等于二直角,
一切物体都是可以分割的这话一点也不错。
第五,我要求他们长时间地继续思考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本
性,此外我还要求他们虽然考虑到在其他一切性质的观念里,都包
含着可能的存在性,可是,在上帝的观念里,不仅包含着可能的存
在性,而且还包含着绝对必然的存在性。因为,仅仅从这一点,他
们绝对用不着推理就可以认识到上帝存在。显然,对他们来说也将
同样很清楚,很分明、用不着证明的是,二是双数,三是单数,以及诸
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对某些人用不着证明就这样认识了,
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却要用一个很长的论证和推理才能理解。
第六,要求他们在仔细地考虑到我在我的《沉思集》里所说到
的那些关于一个清楚、分明的知觉的各种例子以及模糊、含混的知
觉各种例子之后,要习惯于分辨那些认识清楚的事物和模糊的事
物;因为,用例子来说明比用规律来说明要好些,并且我认为,不谈
到什么东西,任何例子也举不出来。
第七,我要求读者们既然注意到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领会得
清清楚楚的事物中认出什么虚假来,而相反,除非偶然,他们从来
没有在他们领会得糊里糊涂的事物中找到什么真实来,因此他们
就要考虑到,假如他们由于感官的某些成见,或者由于高兴做出的
以及建筑在什么模糊不清的东西上的什么假定而怀疑理智所领会
得清楚、分明的东西,那是毫无道理的。他们用这个办法将会很容
易地认为下述的公理是真实的、毫无疑问的,虽然我承认,假如我愿
意更准确一点的话,其中的许多条本来可以解释得更好一些,并且
应该不是当作公理,而是当作定理提出来,假如那时我愿意的话。